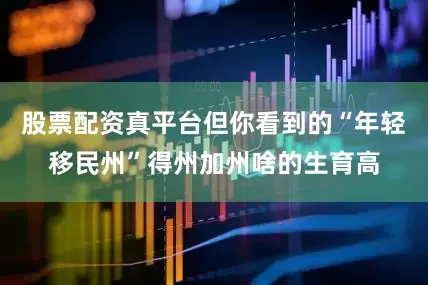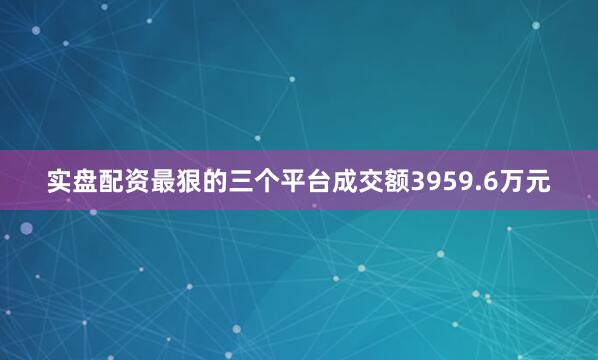醉驾入刑已有14年。近两年,以醉驾为主的危险驾驶罪受到颇多关注,因为这一“第一大罪名”影响着数百万人,同时改革也正在发生。
7月21日晚,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2025年上半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。数据显示,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危险驾驶罪一审案件12.1万件,同比下降14.96%,降幅明显。
自2023年12月“两高两部”发布新的司法解释优化醉驾入罪标准以来,危险驾驶罪案件起诉、受理数量在持续下降。不少人在期待拐点出现,不过,最高法称,上半年危险驾驶罪案件仍居刑事案件第一位。
增设前:醉驾事故引起民愤,严惩醉驾呼声日益高涨
“醉驾具有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危险性,因而醉驾入刑具有明显的预防性刑法的性质,是一种抽象的危险犯。”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兴良此前指出,立法机关试图由此减少醉驾导致的重大交通事故,从而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。
我国在2011年完成醉驾入刑,对应的罪名是危险驾驶罪。当年审议通过的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增设这一罪名,规定了两种类型:一个是醉驾,一个是追逐竞驶,在2015年增加到四种类型。入刑之前,醉驾是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政违法行为。
展开剩余85%醉酒驾驶为何要入刑?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,醉驾导致的多起重大交通事故是直接的推动因素,如2008年底的成都孙伟铭案、2009年的南京张明宝案。孙伟铭无证醉驾,造成4死1重伤;张明宝醉驾,造成5死4伤,二人都触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,被判处无期徒刑。
这期间,民众要求严惩醉驾的呼声日益高涨。2010年,时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,建议在刑法中增设“危险驾驶机动车罪”。在此背景下,醉驾入刑提速。
增设后:案件量逐年攀升,2018年成为第一大罪名
醉驾入刑初期,官方释放严打的信号。公安部在2011年专门发布办案意见,指出“对经检验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,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”。最高检也曾表态,对于醉驾案件,该批捕批捕、该起诉起诉。
由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法律适用存在争议,2013年,“两高一部”发布司法解释,明确: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,只要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/100毫升以上,就属于醉酒驾驶,当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。这一标准沿用了当时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对醉酒驾驶的认定。
此后,危险驾驶罪案件量快速增长。记者查询官方通报,从全国审判数据看,危险驾驶罪在设立第三年就排到了所有罪名中的第三位。
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,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及危险驾驶罪,从2011年5月入刑到2012年,全国法院共审结危险驾驶案6.6万件,判处6.6万人。随后逐年攀升,到2019年,达到31.9万件。
在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,最高法审管办负责人介绍,2023年,人民法院刑事一审案件收案123万件,居首位的是危险驾驶罪。“从2018年起,此类犯罪占比就高居首位,且呈现快速增长趋势,2023年危险驾驶罪同比上升15.3%。”
有多少人因危险驾驶成为罪犯?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2021年接受采访时提到“每年超30万”。虽然危险驾驶罪对应的行为不只醉驾一种,但最高法之前发布过一份报告,分析了2014年至2016年前九个月的危险驾驶罪数据,其中醉驾占比99%。
中南大学法学院张杰在文章中提到,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,截至2024年初,全国至少有超过200万人因此获罪。
同时,醉驾入刑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效果。公安部曾公布数据,在增设危险驾驶罪之后,我国每年因为醉酒驾车导致死亡的人数至少减少200人。2022年,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,酒驾、醉驾的发生率明显下降。
改革呼声:进入轻罪时代,一味打击不能实现预期治理效果
有学者指出,增设危险驾驶罪之后,进入刑事程序的案件远超出官方预计的数量。
当前,我国的犯罪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,轻罪案件占比已经从1999年的不到55%上升至近年来的85%以上。在轻罪成为我国犯罪治理主要对象的背景下,实务界和学界一致认为,轻罪治理要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,并不是一味地打击就能实现预期的治理效果。
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此前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也指出,我国传统治罪模式强调从严打击犯罪,司法实践中存在的“重打击、轻治理”现象,不仅造成治理越来越困难,还带来了不少打击“副产品”。尤其对于人身危险性低、主观恶性小的轻微刑事案件,过于强调打击只会带来更多的衍生案件及矛盾。
我国刑法设置了犯罪前科报告制度:受到刑事处罚的人,在入伍、就业的时候,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,不得隐瞒。这个制度设立的初衷是预防再犯罪。但严苛的犯罪附随后果,让前科人员在回归社会时面临较大的障碍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审查报告中指出,有的地方株连、波及前科人员的亲属,使他们的正当权利也受到限制。
“一个人犯了轻罪判了几个月,但是犯罪记录可能会跟随一辈子,后续找工作、子女升学等都受影响,这就意味着一个本来是轻微违反法律的人,可能会被推向社会的对立面。”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车浩此前在谈及轻罪治理时指出,这是成本、收益上的严重不均衡。
基于庞大的群体成为罪犯,以及回归社会后受到的限制,越来越多的声音提出,醉驾入刑的标准偏低且单一,随着刑法中增设的轻罪罪名增加,社会个体成为罪犯的风险在加大。
改革进行中:优化入罪标准以来案件降幅明显,且有望迎来犯罪记录封存
于是,在建立轻罪治理体系的整体部署下,醉驾治理成为改革的突破口。2023年12月,“两高两部”发布《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》。与十年前的司法解释相比,最大的变化就是优化了入罪标准。
新的司法解释没有改变醉驾的标准,但改变了之前“超过80毫克一律入罪”的司法实践。通过把“具体情节”考虑进去,设置了血液酒精含量每百毫升80、150、180毫克三条线。首先,在80至150毫克之间的,如果没有司法解释规定的从重处理情节,不再刑事立案;其次,对于150至180毫克之间的,如果没有规定的恶劣情节,则适用缓刑;超过180毫克的,则判处实刑。
最高法李睿懿等人在《〈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〉的理解与适用》中解释了优化入罪标准的原因。文章指出,人民法院受理的醉驾案件量自2018年起超过盗窃案件,连续数年位列刑事案件收案首位,不仅与多年来交通肇事、严重暴力犯罪数量持续下降形成反差,也不符合我国社会治安形势和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向好的趋势。醉驾属轻罪,但犯罪附随后果与其他重罪并无不同,因醉驾成为罪犯,不仅个人事业、生活和前途命运受到影响,也不利于家庭和谐、社会稳定。
新的司法解释自2023年12月28日起施行。在发布2024年上半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时,最高法指出,新司法解释实施半年效果显现。2024年1月至6月,危险驾驶罪案件一审收案14.3万件,同比下降12.93%。
今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,2024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危险驾驶犯罪32.4万人,起诉27.6万人,同比分别下降41.7%和16%。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,2024年人民法院审结的一审刑事犯罪案件中,危险驾驶罪案件为27.51万件,同比下降17.48%。
一方面是入罪标准的优化,防止更多人成为罪犯;另一方面如何让他们更好回归社会,国家也作出改革部署。
2024年7月,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数百项改革任务,其中一项是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。此后,《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(2024—2028年)》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》均对此作出回应,明确推动建立这一制度。
我国刑法并没有区分轻罪、重罪,因此如何界定“轻微犯罪”将是这一制度确立的关键。学界和实务界通常将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管制、拘役的犯罪界定为轻罪。观点普遍认为,最高刑为六个月拘役的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轻微罪。
至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何时、如何确立,目前尚无官方定论。此前,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喻海松在文章中提出,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属于立法层面的问题,无法在司法层面自行突破。就立法推进而言,最为理想的状况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联动修改。短期内修改刑法的可能性不大,可以考虑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方式在程序法层面先行开局,待刑法再次修改时再予补充,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有序衔接。
记者 行海洋
编辑 张树婧
校对 李立军
发布于:北京市配资客户体验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